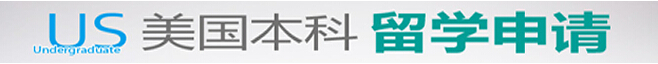|
国际关系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国际社会之间的外交事务和关系,如国家、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国际关系既是学术的领域,也是公共政策的领域。 作为政治科学的一部分,国际关系也和哲学、经济、历史、法律、法学、地理、社会、人类学、心理学,文化研究紧密联系。从全球化到领土争端、核危机、民族主义、经济发展、恐怖主义、人权,都是国际关系研究的议题。 理论 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是为了反对自由主义而产生的,他们否定国家之间会互相合作。早期的现实主义者如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主张国家都是自私的、追求权力与国家利益的理性参与者。任何国家间的合作都只是意外造成的。现实主义者以二战来证明他们的理论。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经典的作家如修昔底德、马基维利、和托马斯·霍布斯都时常被现代现实主义者视为是现实主义的奠基者。不过,尽管这些作家的作品可能支持现实主义的学说,但他们都不曾自称为现实主义者。 新现实主义 新现实主义主要是来自于肯尼思·沃尔兹(亦译做华尔志)(Kenneth Waltz)的著作—不过沃尔兹本人将其称为“结构现实主义”。在保持现实主义以经验为依据的观察上,国际关系是由互相对立的关系所组成的,新现实主义者指出这是国际系统的无政府架构造成的。他们拒绝解释国家内部的特征,主张国与国之间因为相对利益和平衡而不得不对抗权力的集中。与现实主义不同的是,新现实主义试图采取科学和更为实证性的方式。 自由主义/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可以被视为是第一个国际关系的理论。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浮现,以解决国家在国际关系上控制和限制战争的无能。早期的拥护者包括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以及英国下院议员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安及尔主张国家互相合作才能获得更多利益,而战争所带来的毁灭注定是没有益处的。不过自由主义的理论要直到被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嘲笑为空想主义 (utopianism) 后才被定型。 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在美苏相对和解的八十年代取得了发展,试图更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他们同意新现实主义主张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要参与者的理论,但仍认为非国家的参与者和国际组织也应该被认真看待。拥护者如约瑟夫·奈伊(Joseph S. Nye)从博弈论出发,主张国家会不只考虑相对利益同时也考虑绝对利益,因此国际之间除了竞争之外,互利合作的情形也并不少见。在冷战里对国际组织的依赖增加也使得新自由主义被称为自由制度主义(liberal institutionalism)。同时,新一代学者麦柯·多尔 (Michael Doyle) 则改良康德的学说,推广出新的民主和平论 (democratic peace theory),开创了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支流。 国际社会理论 国际社会理论(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ory)聚焦于国家之间共有的基准和价值观,以及它们管理国际关系的方式。这样的基准包括外交、秩序、和国际法。与新自由主义不同的是,他们并非采取实证的方式,同时由于此一学说兴起于英国和澳洲而不是美国,因此也被称为英国学派 (The English School)。这些理论家专注于人道的国际介入(国际人道干预)上,并将其分割为两种群体,一种团结主义的群体拥护人道介入,而另一种多元论的群体则强调主权的观念和秩序。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反对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对于国家冲突或合作的观点;相反的他们专注于经济和物质上的观点。他们假设经济是高于其他一切问题的;强调阶级是主要的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国际系统是结合了资本主义制度追求资本聚集的结果。也因此,殖民时期带来了殖民地的原料,也带来了控制的殖民地市场以供出口,而殖民地自治化带来的则是新的依赖殖民国的形式。 马克思主义的依赖理论 (Dependency Theory 或 World Systems Theory) 主张,发达国家为了追求权力,借由政治顾问、传教士、专家和跨国企业渗透开发中国家将其融入资本主义体制内,以此占用他们的自然资源,并使他们必须依赖发达国家。 马克思的理论在美国较少受到注意,但它在欧洲和其他地方较为常见。 社会构成主义 社会构成主义(Social Constructivism,亦称建构主义)试图将一些后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和实体论前提与实证主义的理论结合。它的拥护者宣称他们是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理论的综合。社会构成主义专注于那些定义了国际系统的权力上,它的创始人—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指出无政府状态便是由国家造成的,意味着国际架构并非只是限制在国家的行动上,事实上也包含了国家媒介的本体和利益所促成的行动。 不过,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两派都提出了批评:后实证主义者主张专注于研究国家会造成其忽略了种族/阶级/性别,使它成为另一个实证主义的理论。而(新)自由主义/现实主义的支持者则认为社会构成主义抛弃了太多的实证的假设,因此不能被视为实证主义的一种。 批判理论国际关系 批判理论跨越多种社会科学,在本质上而言也不仅限国际关系。拥护者如罗伯特·寇克斯(Robert Cox)和 Andrew Linklater 强调人类对于解放的需要,因为国家减少了在提供个人服务和安全上的角色。因此,这种“批判”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以国家为中心的。 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包含多种理论流派,不可能出现一个完整的列表。有人认为女性主义、依赖理论(Dependency theory)、和构成主义都算是批判理论的分支。 后实证主义/后结构主义理论 后实证主义的国际理论试着结合各种形式的安全问题。他们主张国际关系是以研究外交事务和关系为主的,国家和非国家的参与者都应该包含在内。与一般研究高层的国家政治不同的是,国际关系也应该研究世界上较为平常的国际政治—包含了高层与低层的政治部分。因此,一些议题例如性别(通常以女性主义为名突显女性附属于男性的关系—虽然最近一些女性主义也允许加以逆转)和种族(例如没有国家的参与者例如库德族或巴勒斯坦人)都是与国际安全有关的—替代了传统上专注于外交和战争的国际关系研究。 后实证主义的理论经常明确地提倡一种伦理学的国际关系研究基准。这在传统的国际关系里通常被排除,因为实证主义的理论在实证的真相和判断的基准之间已经划清了界线—而后实证主义者则主张理论是由现实所构成的;换句话说,由于不受权力影响的知识并不存在,因此完全独立而真实的理论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后实证主义理论并不试着按照科学或社会学的方向进行。相反地,他们试着以研究有关问题的方式来讲述国际关系,以判断国际现状是如何提升某些权力关系的。 一些例子包括:女性主义(“性别之战”) 后殖民主义(挑战欧洲中心的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的概念 系统层次的概念 联合国大楼国际关系时常被视为是一种分析的层次,系统层次是指那些定义并形塑了国际环境的观念,在国际层次上就如同无政府状态一般,没有一个世界政府的存在。 力量在国际关系上的概念可以被形容为一国拥有的资源、潜力、和国际影响力的程度。这通常被分为硬力量(Hard power)和软力量(Soft power),硬力量指军事、经济力量的使用,而软力量则指源自于文化、政治制度和外交政策有好与否的“吸引力”有关。 极化(Polarity)在国际关系上指的是国际系统里的权力分配。这种观念在冷战期间浮现,当时国际系统是由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所主导的。在1945年以前的国际系统则被称为多极,被许多大国所主导。苏联在1991年的瓦解也使许多人将美国视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体现了单极的国际体系。而有人认为19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崛起、美国渐渐衰弱造成了无极的国际体系,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真正被视为极。 一些国际关系的理论都是以类似冷战的两极观念为基础的。 权力平衡(Balance Power)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盛行欧洲的理论,这个理论主张国与国之间结盟带来的彼此制衡,将能达成国际体系的稳定并维持和平、避免战争。不过由于战间期当中自由主义相当盛行,因此权力平衡理论不那么被重视。不过权力平衡理论在冷战期间再度崛起,成为肯尼思·沃尔兹新现实主义的中心机制。从这个理论上,发展出制衡(权力之间互相制衡)与选边站(国家选择与哪一方结盟)的概念。 霸权稳定论(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也是从极化衍生的概念,尤其是在单极化的国家上。霸权是在国际系统里拥有单极优势的权力,霸权稳定论主张由霸权国家建立全球性的制度来提供公共财,霸权与其他国家之间都能在其中受惠,这种情况的结构是稳定的,因为霸权势力和其他国家都能在这种国际体系中互相合作。这与许多新现实主义的主张相反,尤其是肯尼思·沃尔兹,他主张冷战的结束和单极霸权的出现是一种不稳定的结构,并且会不可避免地改变。 许多支持现行国际系统的人认为目前世界上的国家越来越互相依赖,彼此都对其他国家有所责任和依赖。支持者指出全球化—尤其是国际间的经济互动逐渐成长。国际组织的角色以及在国际系统上各国对一些运作原则的广泛接受也强化了互相依赖的理论。 依赖理论(Dependency theory)是时常与马克思主义连结的理论,主张核心国家会去剥削边陲国家以增进自身的繁荣。许多从这种理论衍生的不同版本要不是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标准的依赖理论),就是使用这个理论以强调改变的必要性(新马克思主义)。 国际关系的系统工具: 外交是各国的代表们进行谈判的动作。在很大程度上,其他所有国际关系的工具都可以被视为是外交的失败。 制裁通常是外交失败后最先被使用的解决方式,同时也是确保履行协约的主要工具之一。制裁可以是外交上或经济上,制裁并切断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的交流或贸易。 战争是对于武力的使用,通常被视为是国际关系的最终手段。克劳塞维茨对此提出了一种说法:“战争是政治的延伸”,不过这并不被广泛地接受。近来对于非国家牵涉的“新战争”(如恐怖主义)的研究也逐渐增加。研究战争的国际关系子学科被称为“战争研究”、“安全研究”或“战略研究”。 国际羞辱的动员也可以被视为国际关系的一种手段。在国际层次上借着“贴标签和羞辱”(name and shame) 的方式来改变一个国家的行为。最突出的例子是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所发布的1235号决议,公开地披露那些违反人权的国家。 单位层级的国际关系概念 在分析层次上的单位层级时常是以国家作为单位,以解释国家单位的部分,而不是解释一整个国际系统。 政权形式:一般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权形式能够支配它在国际系统上与其他国家的互动方式。 民主和平论是一种主张民主国家之间不可能出现战争的理论。主张民主制度使得一个国家的政策基准具体化,只有在正当理由下才能对他国发动战争,而且民主也促成互相的信任和尊重。 共产主义则提倡世界革命,同样也是主张这样能使全世界和平共存,根基于一个无产阶级的全球社会上。 修正主义/现状:国家可以依照他们是否接受目前的现状来分类。修正主义国家企图在国际关系的规则和实践上进行根本的改变,对于当前的现状感到不满。他们认为当前的国际系统是由西方国家所创立以维持自身优势的。举例而言,中国原本属于渴望改变现状的国家之一,但近来已经倾向于维持现状,因为现在维持现状对他们较为有利。 宗教也时常被视为是一个拥有正常国家在国际系统里的行动效力的组织。宗教是一种有组织地原则,尤其是在伊斯兰国家,而政教分离论则是在这个光谱的另一端,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便支持分离政治和宗教的关系。 个人或子单位层级在国际关系里以国家为单位所进行的解释也能运用至其他的理论方面,而不限定在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关系观点。 国际关系的心理学因素:将心理学因素的解释用于国际关系,是来自于现实主义所主张的:国家并非只是一个看不见的“黑盒子”,外交的决策有许多其他的影响因素。检视人性在进行决策时的过程也可能提供一些解释的力量,因为许多参与者可能接收了错误的资讯。团体迷思的现象便是将子单位层级的心理学因素套用至国际关系的经典例子。 官僚政治:官僚政治专注于研究官僚在决策上所扮演的角色,并认为最后的决策其实是由官僚们斗争所产生的结果。 宗教、种族、和分离主义团体:将这些方面作为子单位层级来研究时,能够解释一些种族冲突、信仰战争的原因,以及其他并非国家单位的实质参与者。这在研究近代以前国家微弱的世界时特别有用。 国际关系的组织 国际组织组成了当代国际关系不可或缺的部分。许多国际系统层次的互动都是由参与者自身管制的,他们也否定一些传统的国际关系制度和实践,例如以战争作为解决的手段(除了自卫之外)。 联合国 联合国是一个国际组织,它将自身定义为“一个以促进全世界政府在国际法、国际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平等上的合作的联合组织”;联合国是最为突出的国际组织。许多合法的组织也都模仿了联合国的组织架构。 国际法律实体 法律 国际法庭 欧洲法院 人权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将会被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取代) 人权委员会(Human Rights Committee) 欧洲人权法庭(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美洲国家间人权法院(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国际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地区性安全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东南亚国家联盟 阿拉伯国家联盟 经济组织世界贸易组织 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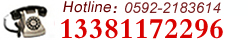

 研究生留学
研究生留学